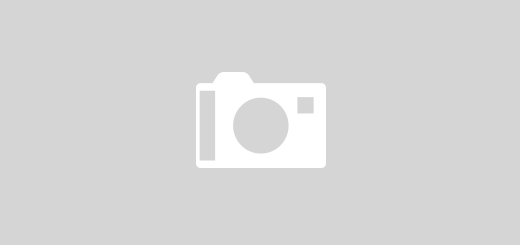经验者之家|健康信息:艾滋病人 真实照片(男人在哪能看出艾滋病)……
123456789


2022年5月12日,“爱之方舟”创始人、联合国“贝利·马丁”奖获得者孟林即将迎来60岁生日。
此时,距离他被确诊为艾滋病已经过去了27年。
作为中国确诊的第一批艾滋病患者,也可能是中国寿命最长的一批患者,孟林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绩。
他成功的部分原因是他奇迹般地抵御了艾滋病。
另一部分源于艾滋病本身带给他的特殊使命:作为一个天然的“幸存者”,他在艾滋病治疗和护理领域取得了卓越的社会成就,几乎奉献了余生。
但是,熟悉孟林的人都知道,总有两堵高墙挡在他面前。
二十多岁的孟琳,在人生充满无限可能和希望的阶段,为自己筑起了一堵秘密的墙。
他建立后,自己的那堵墙,在他最需要社会认同和家庭寄托的年纪,被大家发现并推倒。
孟林的尊严散落在废墟中,在他的生命面前,艾滋病的高墙已经拔地而起。
这一次,他的生死悬在墙上。
高墙之下,波涛汹涌,近三十年,孟林陨落救赎,在其中起起落落。
回望这段异于常人的人生旅程,他发现自己爬不出去的不是伦理道德之墙和生死之墙,而是时代和社会造就的观念壁垒。
开端:揭开的秘密和埋藏的危险
1988年,北京一家不知名的小报刊登了一则小新闻。
文中提到西城蔬菜公司一男同性恋被确诊为艾滋病,这是北京首例确诊病例。
对于当时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新奇的娱乐故事。
然而,对于另一群人来说,这个消息在他们中间引起了巨大的风波。
他们的圈子很小,在社会上能藏身的地方更小。
这个本地男同性恋身份的曝光,给他们带来了两大危险。
一个是铁的事实:艾滋病会死人;
二是可怕的联想:他们的秘密身份、爱好甚至生活轨迹,都会被无数像这位确诊患者一样的北京小报公之于众。
当时26岁的孟林也很快得知了这个消息。他不能像第一组那样冷眼旁观,但也没有像第二组那样惊慌失措。
起初,孟林只是静静地看着。
过了一段时间,他多少有些庆幸,因为经过几次串联和排除,他逐渐发现自己和确诊患者基本没有交集的可能。
更何况孟林的身体很正常,这让他相信自己是幸运的。
沦陷:被判决的人生
和许多八九十年代的同道中人一样,孟林曾经小心翼翼地生活在狭小的柜子里,以保持自己在“正常社会”中的尊严。
其实早在西城区这起案件曝光的前一年,孟林就被抓进过派出所一次。
当时公安机关出于维护治安的目的,将孟林的情况告知了他所在的单位,后者选择了开除孟林。
一方面,他悄悄换了工作,没有告诉家人,另一方面,他更加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这个秘密。
在他们的圈子里,孟林是一个洁身自好、不惹事的人。
但与此同时,社会层面也在发生一些巨大的变化。
1988年艾滋病病例后,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被确诊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这种疾病引起的严重感染、恶性肿瘤以及包括结核病、脑炎、肺炎和肠炎在内的一系列复杂问题逐渐引起社会恐慌。
事实上,向前看,直到1981年,世界才有了第一份关于艾滋病的官方记录。
到1982年,这种新的传染病已经蔓延到所有的大陆。
在过去的几年里,即使医学界绞尽脑汁,也没能研制出一种治疗艾滋病的特效药。公众对艾滋病的认识更是凤毛麟角,艾滋病患者成了避之不及的祸害。
为了加强控制,1991年,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正式设立了男同性恋人群艾滋病感染专项研究项目。
各方都配合并介入,包括北京的公安部队。
很快,一些过去的档案被翻了出来。
所有有前科的男同性恋都被强制隔离,通知直接寄到他们家,比一万份北京小报还厉害。
对于孟林来说,1991年之前,即使他的秘密“内阁”很小,但还是有一点喘息的空间空。
然而,1991年,这场雷霆万钧的“专项行动”突然打破了他的柜门。
他看到自己失望而坚定的家人站在柜子外面,刹那间觉得柜子一打开,空气就涌了进来。
相反,他被掐住脖子,再也无法自由呼吸。
被单位抛弃的时候,孟林还有地方住。被家人抛弃后,孟林搬到了外地,在流离中逐渐自暴自弃。
在孟林自己的记忆中,他承认离家后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因为看不到明天,我也放弃了之前的谨慎和责任感,开始走到哪里就睡到哪里。
当时社会各界加大对艾滋病关注的初衷是为了救一部分人。
但由于一些不成熟的认知和错误的处理方式,名誉的丧失和信仰的崩塌,在这些人得救之前就把他们毁掉了。
从那以后,有些人就完美和谐地躲在深不见底的人群中。
他们的朋友,妻子,孩子,直到死了才知道自己内心最深处的需求。
还有一些人像孟林一样,陷入了放纵和滥交的漩涡,从而增加了患病的风险。
1995年,孟林发现自己的身体开始出现各种问题。
怕被抓被隔离,他一直拖到出现严重并发症才去医院验血。
检测结果出来后,很多医院都以无法治疗为由拒绝。
此时是1996年春节前夕,孟林独自站在冰冷的大地上。
他意识到好心的医生医疗系统已经抛弃了自己。
2019年,57岁的孟林在自己的微信官方账号中记录了自己的感受:“原来生病也是活该。这个原罪让我再也没有做过好人。这是当时给我的结论,我默默接受了这个判断。”
挣扎:存在的必要
当痛苦来临时,就像五脏六腑被撕裂,如果绝望,孟林当然想到了自杀。
但是在跌到谷底之前,孟林得到了机会。
到1996年,中国艾滋病研究的尝试取得了初步成果。
在成千上万不顾一切投身于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事业的人们中,孟林有幸见到了感染科主任徐连志。
成为当时最新疗法“鸡尾酒疗法”的临床试验对象,开始接受进口抗病毒药物的治疗和特殊观察项目。
这根线就像一棵树的幼苗。社会援助、医生的拥抱和健康的逐渐恢复给了它希望的养料。
它越来越强大,生根发芽,生出了更多的求生欲望,后来也给孟林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2004年,接受抗艾滋病治疗8年的孟林,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与同期接受观察治疗但去世较早的他的病人相比,孟林还活着,这让学者专家看到了希望。
很多组织向孟林抛出橄榄枝,希望他以自己抗病毒治疗的经验加入NGO工作。
外界再次向孟林聚集,向他伸出援手。
他从他们手里接过了免费用药的承诺,解决了他看病的后顾之忧,也接过了另一个沉重的东西:责任。
为了让更多的艾滋病患者从他身上看到生命的希望,他必须继续活下去。
在投身于艾滋病药物倡导事业的同时,孟琳逐渐步入反歧视领域。
他做过演讲,写过青春文章,也骂过红脸白脸的人。
从2004年到2019年,孟琳参加了无数的论坛和峰会,组织了多次联合请求和专项调查项目,作为大小机构、基金会、社区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参选,并逐渐建立了自己的研讨会和社会企业。
在与艾滋病共存、以艾滋病为职业的那段时间里,沉浸在工作中的孟琳自然表现出了很多新的东西。
这其中,有孟林不断提升的社交能力,有他不断积累的知识、思维和视野,也有他不断迭代更新的自我认知。
随着个人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基于多次与不同机构斡旋、谈判、宣讲的经历,孟林不知不觉从一个弱小的艾滋病患者,变成了艾滋病领域极具话语权的资深代表和权威人物。
他的名字在中国所有社区中脱颖而出,进入了国际艾滋病研究者的视野。
林禽刻苦学习,不停奔波,为强化社会治疗保障机制做了很多尝试,本质上为感染者和患者提供了慢性病管理的深度支持。
经过二十多年的深耕,孟林浴火重生,重新定义了自己存在的必要性。
把离开当做回归:我还活着,你们好吗?
2003年,抗艾治疗的第7年,孟琳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
他担心离开时自己的形象不佳,所以为自己准备了一幅张清秀的画像,放在客厅里以备不时之需。
转眼间二十年过去了,孟林难免又黑又胖又老,但客厅里的遗像总是那么年轻,甚至看起来都不像自己,孟林和他的遗像生活了十几年。
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孟林从未停止过对“自我”的思考。
他有了自己的一番大事业,接受了社会的一些尊重和认可,也有了自己体面发声的平台和理由。
孟琳于2006年开始了她的博客生涯。
他在博客中强调,虽然没有高超的文字修饰技巧,但他仍然有表达自己的权利。
在上百篇博文中,孟琳积极探讨社会的现状、问题和解决方法,分享自己小狗的生活,慷慨畅谈过往,或给迷茫的年轻人建议和鼓励。
在很多场合,他甚至分享了自己作为同性恋在爱情道路上经历过的渴望、狂热、失落和甜蜜。
另一方面,爱情曾经是孟林“罪”的来源。
很多时候,他会陷入对往事的追忆,基于一种更加成熟稳定的认知,对当时的心情进行判断和分析。
林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少年,青春,一直把自己的秘密埋在心里。
我想到要乖巧懂事有礼貌才能做一个被社会主流价值观认可的好人,也想到自己被警察抓住打成流氓的时候。
关于被抓和被放出柜的经历,孟林痛苦地记录着:“那一天,我承受了自认为承受不起的屈辱,心中的秘密也不再是秘密,就像一个赤裸的野人被羞辱”。
后来在多年的工作中,孟琳习惯了对公众进行大规模的陈述,但另一方面,她仍然无法完全放下对外界声音的恶感。
他生气的时候会忍不住跳出来,在自己的博客或者微信官方账号里粗鲁的骂人。
他认为世界上有两种恶人,一种是无缘无故伤害无辜的人,另一种是对别人的生活指手画脚的人。
孟林基于自己的经历,坚信后者往往比前者更糟糕。
然而,在忙着拯救别人的20多年里,孟林急躁的自己磨炼出了一个全新的自己。
随着阅历和阅历的增加,孟林会选择走进自我反省。
持续思考的结果之一就是断绝与过去病人或同事的联系。
他想离开公众的视线,回到自己的世界去“过正常人的生活”。
2019年,在从事了15年的艾滋病相关工作后,孟林选择了退役。
他爱上了自驾,决定带上自己的肖像,开始一段属于自己的旅行。
有人跟着骂他“你应该让大家坚强的活着,而不是一直装疯卖傻”。
林只是回应道:“这不是我的义务!”
从此,孟林跨越了过去时代和社会强加给他的枷锁,他想通了。
关于爱情,年近60的孟琳对自己说,世界上没有人不渴望两颗心互相帮助。
无论是期待灵魂的对话,还是身体的共融,都不是原罪。
关于尊严,孟琳在与艾滋病27年的相处中,学会了更深刻地理解他人,包容自己。
他向肆意践踏和剥削他人人格尊严的时代宣战,他坚信“我不是你也不是你”。
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人与人之间即使不能完全理解对方,也要保持至少一种尊重。
即使不能完全认同,也不代表可以任意评判对方,羞辱对方。
至于生活,和大多数人一样,孟琳在旅途中遭遇了新冠肺炎疫情。
和大多数人一样,孟林有一个身患癌症的密友——即使不是艾滋病,他的朋友仍然比他先离开。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不管一个人有多忙,多孤立,他的一生中至少有一次会和大时代同呼吸共命运。
关于自由,孟林一方面拥抱那些需要拥抱的人,告诉他们“不要再忍了”,另一方面告诉那些来拥抱自己的人:“好久没有流泪了,只是为了好玩!”
他在解放他人和解放自己的道路上一路前行,这让他获得了新的自由——
第一波疫情缓解后,他匆匆上路。有一天,他在南迦巴瓦的塞拉山拍了一张照片,大声感叹祖国的山河:真美!
孟林离开期间,有传言说他已经去世了。
2021年4月,孟林爬到自己的微信官方账号,发表了最后一篇文章。
在文章中,他淡然一笑:“再有谣言说我死了,我就说,我死了我就死了,哈哈哈哈!”
何曾吹落北风中
孟林正式离开公众视线一年后,连猜测他是否去世的声音都少了很多。
在他的微信官方账号上,有一句他终于用来向外界诠释自己的诗:“宁死一枝香,不被北风吹。”
后疫情时代,社会上涌现出新的“绝症”。
据说,有人因为新冠肺炎而终身后遗症,有人因为网上吵架而产生社交恐惧,有人因为找不到生活的意义而陷入抑郁,有人因为经济形态的恶化而陷入无法治愈的贫困…
人们争相品尝新时代苦难与前进的滋味。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同性恋和艾滋病不再是让人脸色苍白的话题。
在这个新时代真正到来之前,当孟林还在为艾滋病奔走的时候,有人称赞他是一个为所有人付出,为自由开路的勇者,但他对这个名字感到无奈和恐惧。
或许连孟林自己都没有想到,动荡在时代无处不在,只是一个时代的事实在另一个时代变成了“错误”。
一些像孟林这样的微小个体意识到,社会从来没有“正确”的生活,他们不必自始至终自怨自艾。
但消失了的孟林知道,一颗永远向往善良和美好的心,一颗永远珍惜自由和真诚的心,终将引领他走向真正的生活,从此幸福地生活下去。
参考:
《中国的抗艾之路——一个目击者的理论》
反歧视:谁在口是心非
萌林博客:萌小屋
987654321